(我好像寫過自己對實驗藝術的不欣賞,簡以言之,就是實驗本來是為了有作品的,怎麼有人會以實驗,做了幾十年實驗都沒有成品,而拿未成品出來做賣點呢?鄧小宇的文字我是很欣賞的,很絕。他對藝術作品的品嚐能力,也能從這一篇中看到。摘自《鄧小宇》的站借間)
看《夜奔》—— 意料中的榮念曾 2010 年 3 月 明報世紀版

看了藝術節委約榮念曾的《夜奔》﹐感覺和過去幾十年看榮念曾之前的作品沒有兩樣﹔他總能做到不會叫人失望(我指的是榮念曾的作品﹐不是一般的進念作品)﹐但在很久以前開始亦已不再帶給我任何的驚喜﹐甚至連驚奇也欠奉﹐一切都是意料之中﹕那些逐漸增強的音響效果(火車聲、時鐘的答聲、人聲、某些戲曲/歌劇/革命歌曲或佛教誦經聲……)、那些活死人式的緩慢步行、那些單音調的獨白、那些「辯證」式的提問(我是人﹖我不是人﹖藝術是什麼﹖觀眾是什麼﹖有概念先抑或有動作先…… 諸如此類)﹐這一切正好是déjà vu 的最貼切示範。
所以當我看到那本沒有帶給我任何驚奇的演出的場刊寫着〈榮念曾實驗劇場〉﹐忍不住卡一聲笑出來﹔實驗﹖不是已實驗了好幾十年了嗎﹖還在實驗﹖還有什麼尚未實驗過﹐仍需努力﹖不過近年好像連焦媛也組了個團來進行她的實驗了。
正如古人神農氏嘗遍百草﹐在「實驗」的領域﹐榮念曾應該早也嘗遍了所有的可能性﹐而最終得出來的結果﹐這些素材和原料﹐亦有點像將中草藥放入一個又一個藥櫃般﹐都已了有編排、列序﹐每次演出﹐只要打開不同的藥櫃﹐就可以照方執藥﹐又煲出一碗了。
在沒有「劇情」的推進下﹐看榮念曾時我們會特別注重他在視覺與聽覺所下的功夫﹐在這方面他一向都是高手﹐他的編排從來都十分工整、精密、準確﹐synchronization 無懈可擊﹐好一個完整無瑕的拼圖﹐即使在成本的限制下﹐很多時榮念曾總能出其不意製造出幾秒叫人眼前一亮﹐甚至口瞪目呆的視覺效果﹐替整個演出抓到聚焦點﹐這正是我早在1981 年已寫過無妨一年看一次榮念曾的原因。不過今次的演出規模實在太小了﹐而視聽都只能說是差強人意﹐於是他以往的「毛病」、「缺點」就更突顯出來。當中有一個演員喃喃自語不斷在重複﹐有時說﹕我係林冲﹐有時說﹕我唔係林冲…… 是多麼熟悉的榮念曾式對白﹗在我們的榮念曾集體記憶中不總是有著這類相近的獨白﹐不是已聽過有人不斷在重複﹕我係張愛玲、我唔係張愛玲﹐或我係毛澤東、我唔係毛澤東…..將來亦很有可能有人喃喃﹕我係榮念曾、我唔係榮念曾。單是這個「我係/我唔係」藥櫃榮念曾已可以循環永久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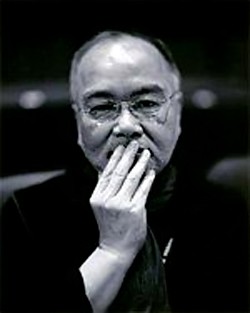
在場刊榮念曾是如此寫着﹕「怪不得大家認為劇場稍不辯證﹐就淪為文化消費的平台……」﹐啊﹐對了﹐「辯證」確是一個魔術名詞、神仙棒﹐亦是他另一個萬應萬靈的藥櫃﹐他每一部作品不是都充斥着大量的「辯證」式的提問﹖像今次字幕就打着﹕
他會不會不夠主動﹖他是不是看得不夠﹖他會不會有些悲觀﹖他是不是想得不足﹖他會不會有些自溺﹖他是不是自以為是﹖他會不會有些犬儒﹖他是不是不夠積極﹖他會不會有些軟弱﹖他是不是不夠自信﹖…… 之後還有二十三個這類要你命的「提問」﹐我不浪費篇幅逐一引述了。
總之全都是發問了等於無問。
其實在榮念曾小小的範疇內他有時真的可以很精彩﹐說是名牌效應也好 (那個姓胡的就連A貨也說不上) ﹐卻正是我這些年依舊不時買票看他作品的原因﹐但這小小的範疇確實容不下他以為可以成功包裝到的大旨題以及要用文字去知會觀眾的sub-text。說實話﹐游清源的文章大部分時間我都看不明﹐但起碼他能給到讀者他好像是在「深入」探討某些「深奧」的東西的感覺﹐於是我也無話可說﹐只能怪自己學養不夠。而榮念曾不斷拿類似上段我引述他自撰的那一連串空洞的口號﹐不管用字幕投射出來也好﹐或由演員背出來也好﹐怎都不能說是在作什麼探索吧﹖深入就更不用提了﹐講到底其實這一切不都是用來嚇/ 壓觀眾的一些門面工夫﹖
在場刊榮念曾又提到他請劇中一名年輕演員用心聆聽他老師唱的一段長達七分半鐘﹐榮覺得是他一生所聽過最入味一次的崑曲﹐然後請那學生說說他聽到什麼。那學生說﹐他聽到先是老師在為別人唱﹐慢慢地在為自己唱﹐最後已經忘記自己﹐為唱而唱。

榮念曾聽了這些話之後﹐「樂了半天」。
唉﹐不說別的﹐古龍金庸的武俠小說我們有那個未讀過﹖那些哲理﹐什麼心中有劍﹐什麼天人合一…… 張三丰聽到張無忌把剛學到的太極招式口訣都全忘掉時﹐也不又是「大樂」嗎﹖這些「最高境界」的「特徵」﹐我們都懂得﹐起碼懂得講﹐賣口乖的孩子也實在太多了。再說榮老師要那個學生聽足七分半鐘﹐然後問他聽到什麽﹐他可以有別的答案嗎﹖他敢有別的答案嗎﹖
而我們的榮老師﹐榮大師﹐竟也就「樂了半天」﹗他能如此自得其樂﹐想來也還是挺幸福的。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